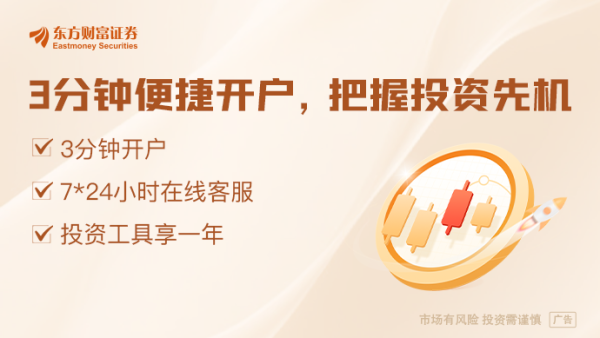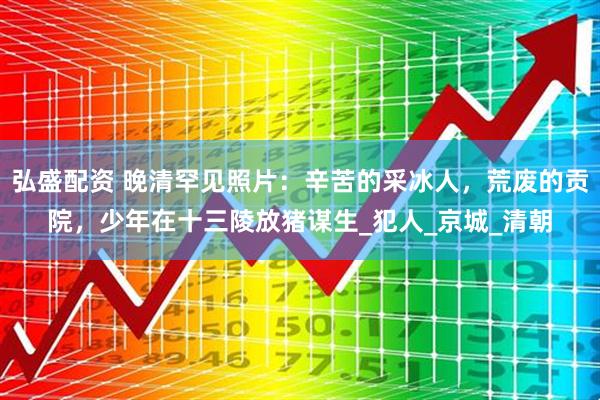
人影散乱,尘世万象,终将成为过眼云烟。试想一百年前的人和事,哪有几人能够记起?摒弃史料,那些泛黄的黑白照片便成了历史的见证。正如古人所言:“念往昔,繁华竞逐,叹门外楼头,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对此,谩嗟荣辱。”也许弘盛配资,若你细心观察,不经意间,你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……
慈禧的葬礼上,曾出现过一幕异常诡异的场景。那时,京城的街道上,送葬的队伍川流不息,所有人群中,尤以那些栩栩如生的纸扎人最为引人注目。这是荷兰记者亨利·博雷尔在1909年拍摄的一张照片,真人大小的纸人竟在大白天显得如此阴森。阴兵开道,纸扎人脸上带着微笑,站在街头,显得诡异而令人心生畏惧。
慈禧是清朝的末代统治者,她于1908年冬去世,紧随其后光绪帝也相继去世。她的葬礼,因陵寝未建成,一直拖延到一年之后才得以举行。尽管阴兵守护,仍未能阻止孙殿英的盗墓行为。仅仅过了二十年,“老佛爷”的尸体便被从棺中拖出,而她随葬的宝物也被彻底洗劫一空,历史的风云变幻,竟如此不堪。
展开剩余80%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痛苦的一段记忆,便是鸦片的侵入。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国运倾颓,百姓困苦,国库空虚。为了缓解财政压力,朝廷竟选择鼓励鸦片种植。然而,鸦片的蔓延,却带来了无尽的灾难。史料记载,那些沉溺毒品的人,情形惨不忍睹。“瘾至,其人涕泪交横,手足无力,不能自举;即便是白刃加于面前,亦唯俯首受死,不敢动弹。”图中的年轻人,甚至已经无法下床,眼前虽是贫困的家徒四壁,却依然麻木懒散,无法自拔。
外国人用坚船利炮撕开了大清的国门,随后而来的,是一波又一波的西方商人、探险者以及间谍。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带来了奇异的景象。在一些晚清的照片中,外国人的身影屡见不鲜,他们雇佣了当地人做佣人,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风景线。
有一张照片中,一位佣人推着独轮车,车上坐着四个皮鞋擦得油亮的孩子。这些孩子是随着父母来到中国的洋人子女。而相较之下,那佣人的脚下仍然是草鞋,身着简陋,与身边孩子的差距一目了然。
照片中,曾有被关进“站笼”的犯人。所谓“站笼”,也称立枷,是木枷的一种变形。立枷的上端用枷锁固定住犯人的头部,脚下垫着木板。若是在酷暑下游街示众,犯人往往在几个小时内因脱水而死,甚至若木板被抽走,犯人也会因无法呼吸而窒息死亡。生死之间,残酷无情。
还有一张照片中,某位水师提督的随身护卫,身着威武的战甲,手持大刀与长矛,神态自若。胸前的“水提前协亲兵”标志显示出他们的身份。那时,热兵器的普及让这些护卫的装备看起来并不那么强大,但他们的威风凛凛,是否能真正保护他们的大人呢?
在另一张青楼女子的照片里,三位女子的全身照展现了当时的标配:刘海和裹小脚。那时,缠足风尚如火如荼,青楼中的女子,也都裹着精致的三寸金莲。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,裹足成为一种手段,甚至成了取悦顾客的一种方式。
卢沟桥上的驼队,是连接京城与外界的必经之路。每当商旅往来,驼铃声便响彻在京城内外。即使是皇帝外出祭拜皇陵或巡视南方,都会经过这座桥。驼队的影像,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记忆。
顺天贡院,曾是清朝求贤若渴之地,是科举考试的重地。而如今,这里杂草丛生,只剩下城门楼孤零零伫立。曾经在鼎盛时期,贡院里有多达一万六千名考生,而如今,曾经盛大壮丽的考棚已经拆除殆尽。八国联军侵占时,这里曾被德军占领,几乎被拆得一干二净。1905年,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在一个寒冷的冬日,河里挤满了采冰的劳工。在清朝时期,北京的采冰工作由内务府与工部垄断,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夏季购买到冰块。采冰的地点通常是在北海、护城河和什刹海等地。寒冬腊月里,采冰人天未亮就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工作,汗水与寒冷交织成一幅艰苦的生活画面。
京城那雄伟的城墙,凝结着古人智慧与坚韧。城墙下,一条土路蜿蜒向前,马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缓慢行进。一边是护城河,岸边竟是光秃秃的,没有一片绿草。即使在这壮丽的城墙下,荒凉依旧无可避免。
在庚子事变中,曾拍摄过一张合影照,其中意大利士兵和清兵并肩而立。在这张照片中,西方士兵身材高大,但清兵的身形却尤为魁梧,他们甚至比外国士兵高出了不少,展现出一幅别具一格的对比画面。
1902年,北京十三陵的神道上,一名少年在石像前放猪谋生。照片中几头猪瘦弱不堪,猪毛都竖立起来,颇为可怜。在那个时代,喂养猪只需数年积累,猪的生长速度远不如今天的养殖方式。这名少年,或许是地主家的长工,生活困顿,家里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,却仍要负担饲养这些猪的重担。
发布于:天津市倍查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